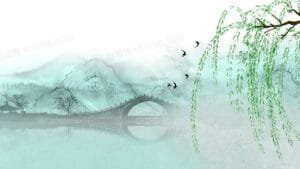
清明上河圖
一直到母親過世,記憶裡才有了清明。在這以前的二十五年裡,清明對我只不過是一個名詞,夾雜著幾句唐人的詩境,就這麼杏花細語,朦朧地過來了。儘管成年以後看不少或圖或文的記載——東京夢華錄裡的清明、清明上河圖裡清明,那些躍然紙面的文字和筆筆欲活的畫意令我悠然神往,但也使我黯然神傷。歷史的街道是沉寂的,繁華裡總帶著幾分淒涼意。很像陳年的刺繡,金線銀線都還暖暖有光,但那繡花人早已不知去向。樓頭倚望,細雨斜陽,只有那隱隱的陳香,猶自眷懷著舊日的旖旎。這是我早年心中的清明──歷史繁華褪了色的縮影。後來無意間讀到一位新詩人的小詩,雖然寫的不是清明,卻總讓我聯想到清明上河圖那座熱鬧的汴梁虹橋。他是這麼寫的:
銀窗下的江南河/在暗夜裡不知從何處來/亦不知往何處去/已是消逝在河上的人呀花呀/不知到哪裡去了
詩題就叫《江南河》,有時候會令人想起日本浮世繪畫家北齋的畫境,不過櫻花世界的虛幻感固然有之,若論到蒼茫沉鬱,便只有張擇端的汴梁虹橋差可比擬了。我不知這位詩人心目中是否想到過南宋的那座橋,但是我,我卻固執的把這首詩和那幅畫牢牢地聯在一起,終至不可開交的地步了。數年後這位詩人又出了一本詩集,叫《端午》,他的詩思一直固著在三齲大夫瀟湘夜雨的情境裡,低弘忘返,而我,我心另有所屬,卻始終執迷在清明在意想中,沉湎不歸……
然而,二十五年來,儘管費盡思量,而我,究竟是不認識清明的。年年四月五日,滿山遍野都是掃墓的人,但我卻置身局外,為賦新詞強說愁而已,可憐我們這一批「海上難民」,根本沒有見過自家的祖墳。海峽裡的波濤,不止把我們從地理上割開了,更把我們從歷史上給剪斷了。三十八年是這樣突兀的一個分水嶺啊,前不見古人,後不見來者,我們從這一塊陌生的土地上重新開始,既不認得死,也不認得生。我們三十八年生的這一代人,究竟是幸運還是不幸呢?萬里外的祖墳即使想夢也夢不到了,歲時祭掃,只是呆呆望著父親點燃燒紙、行禮如儀。早些年在籬笆圍的院子裡,後來又改在公寓頂樓上燒。夜色如漆,火光如魅。父親遙向山川阻隔的天涯拜了又拜,到底是什麼使他這般牽掛?祖先變成了紅紙裝的神位,在幾個大紅棗饅頭的簇擁下,儼然受享。我們孩童在父母監視下,對著空桌空椅三跪就叩,心裡不無納悶。燭花爆跳,睡眼惺忪,猶自眷戀著父親未講完的家鄉故事,蕎麥田、高粱地,男耕女織,騎驢趕集……故鄉的山水啊難入夢,祖先的容顏無處覓食。隻香菸裊裊,化入幽冥,碧海藍天,蝴蝶夢迷離。祖墳不屬於我們了,清明不屬於我們了,壯的老了,小的壯了,歷史向前走,不顧人世的滄桑,他有他自己的方向……
第一次遇見死亡,是外婆的葬禮,癌症對她做了個鬼臉,她就跟它去了。那年我十二歲,永遠不能忘記棺木推入焚化爐的一剎那。哭聲四起,姨媽們搶天呼地,要衝進爐裡,忽然一切都靜了,強大的火焰聲壓過了所有的哭聲,自然的鐵律不由分說決定了一切,慈祥的外婆能唱崑曲、能演戲,靈巧的十指能描花、能繡鳳。她的記憶好到能背電影的台詞至一字不漏,她那絕妙的口才就是十個戲子也鬥她不過。然而,這一切到哪裡去了?她死後,外公整整抄了一整部的金剛經,虞世男的端正小楷,一筆不苟地寫了又寫:「若以色見我,以音聲求我,是人行邪道,不能見如來…… 」,音聲色相俱是靠不住的,鏡花水月本來澄空,這是中國的鎮魂樂,千年來安定了多少無告的心。古典的愛、含蓄的情、綿綿的此恨、渺渺的此身,都寫進了這一筆一筆的勾勒。直到有一天,老先生的筆忽然不動了,微風從經卷上佛過,生命的氣息離開了那裡,外公的死只差外婆兩個月,熊熊烈焰再一次大展神威,而這一次我只記得姨媽和叔叔們哭泣著拾骨灰。太可怕了,這就是生命嗎?記憶裡,外公像是最後一個古典的王孫,他永遠袍服整齊,即使在家也一絲不苟,他雪白的臉子上總是掛著溫雅的微笑,他的談吐溫和有力,文質彬彬,真能做到溫良恭儉讓的境界。他會撫琴、擅書法、精烹調、諫茶藝,一口笛子吹來能響遏行雲,幾十年伴著外婆低唱詞曲,儼然一對神仙眷屬。雖然到台灣來家道沒落了,但生活的藝術仍維繫不輟學。花瓶上的圖樣,盒子裡的香氣,古畫古董,琴畫滿床。這是最後的一對中國夫妻了吧?二十年後我回想,可惜了那個凋零的世代……然而,儘管我被他們認得了死亡,但我仍然對清明一片陌生。
清明還是別人的事,沒有我們的份兒。人家成群結隊上山掃墓,我們只能在靈骨塔燒兩炷香。舅舅帶走二老的骨灰以後,就連祭塔的機會都沒有了。我們還是祭拜我們自家的祖先。三個血紅的神位,幾個碩大的棗饅頭、雞鴨魚肉、鮮花素果、幾盞清酒、一爐香煙。然後是三跪九叩,燒紙送靈,一切禮儀結束在公寓五樓陽台下,而萬家燈火中,四鄰的樓房是越蓋越高了,汽車機車也越來越擠了,人在長,時代在前進,益發顯得這儀式有些脫離時代,有些不合時宜,都市的陰影威脅下,紅燭青煙竟顯得那樣的不調和。但主祭者無視這一切,歲歲年年,行禮如儀,時代有它的方向,但匹夫也有他不可奪的志向!
就這樣,我雖不懂清明,清明卻自己來了。而它的來是那樣的突然,那樣的並不可喜。就在服兵役那年,母親過世了,雖然她心臟病一直不好,但四十六歲就離開世間,也未免去得突然。母親遺言一定要用土葬,或許是外婆外公那兩次火葬給的印象太刺激了?我們總覺得那不像是對待人的辦法。人生固然夢幻一場,究也不能視同垃圾,堆起柴垛,一把火燒了,其場面容許豪壯,但總感覺像是夷狄蠻貊的作風,父親尊重母親的遺志,將她安葬在六張梨的山上,從此我們島上終於也有了「祖墳」,第一個「葉落歸根」的墳。還記得扶靈的素車經過蜿蜒的山道,坐看兩邊有那麼多墳塋,心裡的感覺不勝複雜。這些墓中人像我們一樣的活過、愛過、恨過、恐懼過、得意過、失望過、做過,甚至也實現過種種的夢,而今安在哉?一塊一塊的碑石簡單地敘述其生平大要,但誰會為一個陌生的逝者駐足片刻?俱往矣!金童玉女,皆成塵埃,人生不過是一則白痴講的故事,滿是聲音與憤怒,卻了無實義。我當時默誦莎翁的句子,那麼自然地就湧上了我的唇舌。經過幾番曲折,我們抵達一個比較高的山坡,就在一棵梨樹邊下,為母親安置了永遠安息的地方。再見了,生我養我的人,今生的恩德,來世再報了!長空漠漠,谷風習習,種種往事,驀地湧上心頭。可怪的是,在自幼而壯的成長歷程中,在煙色迷濛的回流裡,我獨記下兩個鏡頭,一是兒時母親為我穿衣,每每要伸手把裡面的衣角拉平。一是母親最後主院時與我同吃最後一碗麵,她的眼神慈愛得令人心悸。或許這便是一種預感吧?我永遠不能忘記那最後的一瞥,人對生命延續的貞定之力,那是生天生地、創造萬物的同一個力量。如果我能在母親墓碑上留字,我要刻的就是「生之守護」四個大字。
埋葬儀式結束之後,不久即是清明了。第一次我識了滿山野的掃墓人潮,真是擁擠啊!我真不懂,為什麼大家一定要都趕在同一天來呢?何不疏散疏散,分批前往?那年不到三十歲的心就是這麼想的。洶湧的人潮使得路程遙遠而緩慢,火辣辣的太陽更是燒出滿頭火氣。我們一家五口,由父親帶隊,隨著人群,慢慢上山。沿路不約而同地談到母親生前的事,並想起外公、外婆,一個比一個遠,最後提到祖父祖母,我們完全沒有見過一面的,更是遙不可及了!但,在心裡,這些人是永遠在一塊兒了。中國人在地上有一個家,身後在天上還是一個家。父親不說,但我們都希望,有一天還是把母親的骨灰帶回老家葬在祖墳裡。到了山頭母親的墳上,遊目四望,父親說這兒的風水還不錯,利子孫。中國人時時刻刻忘不了祖先和子孫,人的意義和價值大半寄託在這個生生不息的生之大流裡,自我是次要的,要緊的是作為生之大流的一個點滴,能夠讓江河永遠不廢地流下去,蔚為波瀾壯闊,連天接地的一個動態的永恆,人沒有我,我在你中,你在我中,你為我活,我為你死,傳宗接代,光前裕後,人能善盡其起承轉合、繼往開來的責任,很可嗔目安息了,這樣的一種人生觀,不就是眼前這個「萬人拜山」、民族掃墓的註腳嗎?站在小山坡梨樹下,我彷彿悟到了一點什麼,有些飄忽。不易把握,但我感覺到,生命有跨入一個新境界,就在母親的墳上,忽然眼界大開。
從此我也有了清明,不止是唐詩宋畫裡的清明,而是實實在在,流淚流汗的清明。雖只是小小的一個墳頭,在我心中卻像靈魂的歸宿。我絕對想不到會對那一棵梨樹、那一座土墳有這麼殷重的感情,父親的感受比我們孩子更複雜,有一年清明,大家站在梨樹下,瞭望四野,無限江山!忽然父親幽幽地說:「三十年前我和你媽相識在大陸海邊,不想三十年後卻親手葬她在小島山頭!」白雲悠悠、長風拂拂,人世的滄桑誰能預料?我在想,如果請上墳的人每個人都來講逝者的一個故事,那嘆息唏噓之聲當是盈天地都裝不下吧!而中國這三十年來的變動,豈不比任何時代都巨大、悲哀?祖父過世了,而這邊不曉得,子孫亡故了,那邊也不知道,多少中國人活生生地被剝奪了奔喪的權利,他們只能慫望雲天,浩嘆無窮。那一道波濤洶湧的海峽,豈不就是中國人內在生命的裂痕?天柱斷、地維折、綱常絕、祖孫散,上帝之鞭狠狠地抽打著濺血的海棠葉,然而蒼天啊蒼天,中國人究竟犯了什麼大罪?古典的中國死了還不夠,還要分屍,分屍不足還要滅跡,滅跡之不足還繼以詛咒!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?海峽裡日夜洶湧著波濤,你們回答這些問題!
漸漸地,來上墳的人減少了。妹妹到美國去了,她到墳上大哭一場,以後還能不能就不知道了。時代紛亂如此,人命無常如彼,烽火戰亂,一夜數驚,明年的事誰知道呢?這一代的中國人,由舊大陸漂到寶島,再由島上飛往新大陸,花果飄零,隨風四散,真有如風中的秕糠,飄泊無定。
送走了妹妹,父親也不能來了。某個夜晚中風擊倒了他,從此半身無力,步履維艱,一枝拐杖,強伴生涯。上墳的行列由六人而五而四,現在我變成了領隊了。身為長子感慨良多,悵望清明憂思何限。時光流轉,夜半真似有力者負之而去來者益少,去者益多,漸漸的,這山坡上搬來不少長輩親友。先是姑丈過世,他就葬在母親的墳墓的山坡下,一個斜坡滑下去幾秒鐘就到了。他的遺像中依舊是一張堅強剛勁的臉,山東人的樸拙、鄉下人的樸厚,黃土平原上的剛毅木訥,這一切在現代化的大都會、商業化的社會裡是慢慢絕跡了。他臨終時躺在病床上,強忍著胃癌的痛苦,還不忘告我說:「宗教不能不信,但也不能太信!」這古傳的中庸之道,發自一個真正迫切需要宗教安慰的臨終人之口,真是令人震驚!如今我呆望著他的遺像,總覺得他有一種不朽,他面對死亡時的莊嚴,不正說明了中國文化強韌的一面?五千年悠久的歷史豈偶然哉,豈偶然哉!歷朝歷代的聖賢豪傑我雖未曾親見,但從古往今來這些平常人身上的堅強和偉大,當是中國僕而復起,愈挫愈奮的主要憑藉。時代演進,文明日新,然而這樣樸實的人格卻漸漸的少了。商業也是正業,但以中國的風土和條件,商業氣質絕不足以為立國的基礎。望著姑丈的遺像,想著今昔的變遷,香煙繚繞中,不勝古國喬木之憂。安息吧,您已完成了一個典型,一個榜樣,我願在你的墓碑上刻四個字:「死之楷模」,任風吹雨打,草沒煙迷,這裡永遠躺著一個人,他的名字,寫在鐵上!
母親過世至今已是八年有餘,八年來的清明,年年不同。這座山上的親戚朋友年年加多,我們的清明節無形間也愈「充實」起來。可悲的是,工商社會繁榮裡包著淒涼,多年故舊老死不相往來,一直到收到訃聞,才有機會再見一面,卻是最後一面。而再見時,常驚呼熱中腸,發現故人容顏已故,全非憶的模樣。逝者的家屬中也盡多不認識的後生輩,益發令人感覺生命的無常。我兒時的那些叔叔伯伯們一個一個的凋零了,那一個動亂苦難的年代,一步一步地遠去了,多少辛酸血淚,不再有人記憶,歷史不會記載他們,只有他們的墓碑,在荒菸蔓草間,憑吊著無窮的遺憾。而做為三十八年落地而未生根的這一代,我心中總覺負欠他們太多。苦難的歲月,憂愁的風雨,那一批海上難民是如何地互相扶助,克服困難,再造家園,那一份同甘共苦,胼胝足的克難精神,當是日後富裕社會的主要基礎。然而社會富裕了、繁榮了,樓高車快、衣輕馬肥,當年同時上船的難兄難弟卻少見面了。財富沖淡了人情,欲求三十年前大雜院裡的溫暖卻渺不可得。只有在清明時節,前往焚香致祭,回想某位叔叔曾天天載著幼時的我上學下學;回想某為伯伯常餵我吃飯,某個嬸嬸抱過我,某為公公曾教我拉琴唱曲,某為老爹曾格我於患難,或幫我繳學費……這種種往事,在歲月裡面像發面似的,越發越大,讓我興起欲報無由之痛。真的,人的善心善行,就算小如芥子,陰微不顯,但永不磨滅,時日一到,就要長成大樹,任誰也砍他不去。正如當年那耶穌所說的:「天國好比一個人把種子撒在地裡,黑夜白天。或睡或起,那種子發芽生長,他卻渾然不覺……」我雖非受洗的教徒,但每想起他們的陰德,總不免在其墓前徘徊良久,默誦基督的訓言,再三不能自己,就算是我的祝福和感激,願他們的遺愛,終將報償在他們綿綿兒孫的身上……
是的,去者日已多,但生的力量究竟大過了死。你看,每年清明,四野的人潮不是越來越洶湧嗎?遠的不說,且看我們家,雖然父親妹妹不能來,但人口卻多過往昔。我們結了婚,有了孩子,最小的弟弟也帶著女朋友,一行人邊走邊聊,好不熱鬧。孩子大聲大嚷的,更增添了無限情趣,嬌嫩的童音,大呼小叫地喊著要找奶奶,更使人覺得像是回家而不像是掃墓,我看別人家,情形也差不多。人山人海的山上,扶老攜幼,浩浩蕩蕩,大家長幼有序,拾級而上,雖然火傘高張,卻沒有絲毫倦容。或彎腰除草,或低頭默禱,或促膝聊天,或焚香祭拜。凝立山頭往下望,但見蜿蜒的山徑上,萬頭鑽動,香花素果,濃香四溢。遠看是一個朝聖的行列,整個民族都投入了。山外儘管煙囪林立,銅臭四塞,但山裡卻是樸實誠懇的古代風味,城市裡疏離的人群又在山間緊緊凝結成一體。由慎終追遠祭拜天地,飲水思源。感恩圖報仁民愛物,物我同春。有憶往事而思來者,生生不息。天人合一,生死本來不隔,物我本來不二,更何況家與鄉、國與族、古與今、聖與俗,一切的一切,都被渾渾然打成一片了。這便是中國人的信仰,這便是中國人的力量,憑著這個,他蕩寇掃兇,憑這這個,他綿延無窮,憑著這個,他一次又一次超越了歷史的劫難,深深安頓了整個民族的大生命。我們能夠樂天安命,又能視死如歸,其秘密就在這些清明的活動裡面──原來清明節就是中國民族復活節啊。
這遲來的頓悟,令我喜不自勝。我不再為逝者悲傷,只因看見了民族的希望。一炷檀香,虔誠拜倒,謹將這一幅永遠畫不完的清明上河圖,呈獻宇宙間至高的那一位,願它時時守護我們、祝福我們
——尚饗!
Canon Music and Arts Online
學習更多︰全方位中文課程
